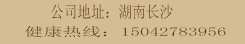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地产 > 族际和谐马克思主义关于大小民族关系的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地产 > 族际和谐马克思主义关于大小民族关系的

![]()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地产 > 族际和谐马克思主义关于大小民族关系的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地产 > 族际和谐马克思主义关于大小民族关系的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列宁和斯大林在批判“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上留下了大量著述,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处理大小民族关系的经典论述。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牵涉的不仅仅是民族关系,而且涉及苏联与其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方面有很多理论贡献,但在具体论述上和列宁有分歧。斯大林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逐渐减少和消失,“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为他打压政敌和“异见”的“棍棒”。经典作家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是其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因为不论列宁还是斯大林对于两种民族主义的论述都是和苏联国家构建联系在一起的。苏联的国家构建最终是一种失败的结局,从民族角度看,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不力的原因,更有其天生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难。我们学习列宁和斯大林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要有一个整体观,既要着眼于这一理论对大小民族关系的重大意义,也要透过这种关系看到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大国的国家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多民族国家建设
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是在不断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其著作中提及和批判的“民族主义”种类繁多,但批判最为着力的是三种:一是“党内联邦制”,二是“民族文化自治”,第三就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或称“两种民族主义”。就时间上来说,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和斯大林着重批判的是前两种,十月革命之后,就集中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了。两种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表现于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处理大民族和小民族的关系始终和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分不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没有涉及大小民族关系问题,而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就成为正确处理大民族和小民族关系乃至全部民族关系的关键问题了。列宁和斯大林在批判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上留下了大量著述,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处理大小民族关系的经典理论。回顾和学习这些著述对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多民族的国家建设很有必要。
一、列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基本论述
年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对明确的“两种民族主义”论述不多,但也多次提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将其视为俄国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称其为“反动或黑帮民族主义”,它“力图保证一个民族的特权,而使其余一切民族处于从属、不平等甚至根本无权的地位”。列宁认为沙俄政府的政策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精神,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少,使它们彼此隔绝并煽起它们之间的仇恨。
然而列宁又发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形式,表现于不同的群体。“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当时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即当代整个资产阶级,也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往后又产生了“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民主派”,以致于出现了“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这样,在列宁笔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成为大俄罗斯民族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都可能有的民族主义,包括沙皇君主集团及其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包括俄罗斯资产阶级及其所谓的“自由派”“民主派”,也包括一般的农民和其他阶级的人。列宁曾说,自由派(进步党—立宪民主党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可以从关于“斯拉夫人”的使命的沙文主义言论,从关于俄国的“大国使命”的言论,从主张俄国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而同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的言论看出来。而这些表现也是和其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别一致的。
实际上,在列宁批判的各种民族主义派别和思潮中,只要是出自大俄罗斯民族成员的,不管是哪个阶级,都可能成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种来源和表现。
沙俄帝国是由原来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从十四世纪起,莫斯科大公利用钦察汗国衰落和内讧之机,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并开始向邻国扩张疆土。特别是从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到年尼古拉二世王朝覆灭的年间,历代沙皇向四周大肆侵略扩张,使俄国版图从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万平方公里,由原来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变成了拥有多个大小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统治集团对被征服民族软硬兼施,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同时在俄罗斯人中散布大俄罗斯主义,制造大俄罗斯民族优越感,形成了歧视非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列宁讲:“大俄罗斯人在俄国占43%,但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却统治着57%的居民,压迫着所有的民族。”而被压迫民族中也不断形成反抗和抵制大俄罗斯民族统治的各种思潮和行动,成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沙俄帝国的形成过程始终是与奴役、掠夺被征服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各周边民族及其国家是沙皇通过武力征服合并到俄国的。因此,他们与自沙皇伊凡四世开始的历届中央政府,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一旦有条件,就会争主权,闹独立,直至同俄罗斯决裂。所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均在于沙皇时代的民族压迫,两种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渗透在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障碍。
正因为这样,列宁在揭露和批判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列宁讲“社会民主党应当注意到,被压迫民族的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往往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掩饰他们离间工人和愚弄工人的意图,暗中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勾结,损害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利益。”列宁提醒说,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厮杀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也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的趋向。
但是,在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力度和侧重点上,列宁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批判远甚于地方民族主义。他在不同的场合一再指出:“不根除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俄罗斯居民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俄罗斯无产阶级“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列宁提出首先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一是因为在俄国,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俄罗斯统治集团实行的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击败这种民族主义是和推翻沙俄封建专制统治完全一致的。二是由于沙俄对其他民族统治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已渗入社会各个层面,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民族联合的努力必须要克服这些偏见和错误认识,包括隐性的、不自觉的民族情绪和思想。斯·格·邵武勉(~年)是一个坚定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与列宁多次讨论民族问题理论,出版有关于民族问题的专著。他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宣传各民族的友谊和团结,不调和地反对民族主义,但在一些问题上和列宁有分歧,包括主张把俄语作为国语在俄国加以推行。年12月6日列宁去信批评他:“俄罗斯语言对许多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起过进步作用,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难道您看不见,假如不搞强迫的话,它本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起进步作用?难道‘国语’不正是驱使大家离开俄罗斯语言的一根棍子吗?您怎么就不想弄明白在民族问题上特别重要的那种心理因素呢?只要搞一点强迫,这种心理因素就会破坏和损害中央集权、大国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使之化为乌有。”列宁在此没有直接谈及大俄罗斯主义,但对隐藏在俄罗斯人内心中的大民族主义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
年12月28日,苏俄内战激战正酣。列宁为即将战胜邓尼金军队的乌克兰人民写了一份公开信,就乌克兰解放后如何建国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问题上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乌克兰完全脱离俄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同俄国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三是与俄国结盟形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列宁在到底该选哪一种方案上没有给出具体的意见,却对大俄罗斯族的共产党人警惕和防止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问题表达了非常鲜明的态度。他说,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没有充分权利的附属民族对大国压迫民族是充满愤慨和不信任的,例如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已经积累了好几百年了。所以,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对民族的不信任心理残余应当采取非常谨慎、非常耐心、肯于让步的态度。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应当坚持要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那样乌克兰人就很容易怀疑,那是出于旧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偏见。“产生这种不信任是很自然的,在相当程度上是难免的和合乎情理的,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害处的。”
年5月外高加索各族人民废除了沙皇时期的“总督府”,分别建立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个独立的共和国,但红军在用苏维埃政权取代这三个共和国后,这一地区就由设在梯弗里斯的俄共中央外高加索局来管理。年10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即将成立,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名义加入苏联。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对此不满,主张三国直接加入而不同意中间再加个联邦。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党比俄罗斯帝国任何一个别的民族共和国的党组织都强大,但他们没有成为独立或自治的党,而是统一的俄国共产党(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局对格共中央的主张进行了严厉压制。先对格共中央领导人做了“党内警告”和撤职处理,继而在对方不满上诉后进一步“改组”了格共中央,奥尔忠尼启则还动手打了格共中央领导人姆季瓦尼。事件发生后俄共(布)中央向梯弗里斯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主任是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也是委员会成员。列宁为此事的发生极为忧虑和痛心,在听了调查此事的捷尔任斯基汇报后两次发病。12月30及31日,正值苏联宣告成立之际,病榻上的列宁口授了一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之后年3月5日和6日又口授了两封信,就处理“格鲁吉亚事件”做后续安排,其中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态度表示愤慨。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是列宁留给俄国共产党人在苏联创建和社会主义事业中怎样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份珍贵文献,也是其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献。这封信是12月30日和31日两次口述完成的。前半部分,即30日部分首先对自己因病没能“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而深感内疚,“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对在筹建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统一机关”的存在而使“退出联盟的自由”变成“一纸空文”而严重不满,因为“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同时他还说:“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之后他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在调查格鲁吉亚事件中表现出的“俄罗斯化的异族人”的“过火情绪”、对直接处理该事件的奥尔忠尼启则表现出的粗暴行为做了严厉批评。还在这个事件之前,年10月6日列宁在给俄共(布)中央的另一重要领导人加米涅夫的一个便条中写道:“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牙吃掉它。”可见当时列宁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痛恨之情,与此相应,列宁在这里把以前常用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改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在31日部分,列宁进一步表达了大民族的无产阶级在对待小民族问题上应有的态度,他认为: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感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在该信的“续记”部分,列宁表示应当保留和巩固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同时表示不能允许有人借口统一而“干出大量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要通过法典和规章来保障各民族共和国的应有权利。提出“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最后提出,应当站在整个国际和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待苏联体制中各民族的关系,“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
列宁逝世前的这篇文章是他留给苏联共产党人的一份重要政治“遗嘱”。他明确阐明了俄国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压迫民族(大民族)和被压迫(小民族)的关系,苏联建国后大小民族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提出大民族要以“让步”和对自己“不平等”的态度来换取小民族的理解和信任,宁肯牺牲新建国家体制上的统一和权力集中也要换取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真心合作。列宁的这一“让步”理论极为必要和可贵,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沙俄帝国的形成是与它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征服压迫联系在一起的,新生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要想巩固原有疆土并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为旧政权在民族关系上造成的巨额负资产“买单”,以完全真诚和平等的态度来联合、团结以前的被压迫民族,而不能有任何的疏漏。这也就是列宁对在格鲁吉亚事件中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极为忧虑、极为愤慨的原因。实际上,列宁在此体现出的大民族和小民族关系的思想也为他设想中的“世界苏维埃联盟”中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确定了原则。因为按照列宁的设想,新建的“苏联”国家既是未来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样板,又是这个联盟的第一步;搞不好样板走不好第一步就不可能有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所以,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牵涉的不仅仅是民族关系,而且涉及苏联一国之内的国际关系以及未来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是和族际主义相连相通的。
二、斯大林的理论贡献及与列宁的分歧
作为列宁的战友和苏联共产党前期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方面也有很多理论贡献,但在具体论述上和列宁有分歧,以致后来又背离了列宁的理论,在实践上走向了自己原初理论的反面。
和列宁一样,斯大林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论述主要在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苏联创建前后。年1月1日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
“俄罗斯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同民族主义倾向作斗争从未有过重大的意义。所有的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员,过去都是统治民族,他们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除了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一般说来,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用不着,或者几乎用不着去克服这种倾向。
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党员是经历过民族压迫阶段的被压迫民族的儿女,他们与此不同,他们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残余,因此克服这种倾向和铲除这些残余是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的当前任务。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阻碍了我国东部共产主义的形成。”
显然,斯大林在此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着力点放在了非俄罗斯族的“突厥语系民族”,对大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则做了开脱。这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斯大林本身是格鲁吉亚人,属于非俄罗斯族;二是这是斯大林在“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上的讲话。从这两个因素来看,着重对“突厥语系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提出批评也合乎常理。此外斯大林对非俄罗斯族中的民族主义如此重视,也与当时这些民族地区存在着的具体形势有关。年7月6日斯大林在文章中揭示了格鲁吉亚和其他南高加索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增长了,对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绪加深了:反亚美尼亚的、反鞑靼的、反格鲁吉亚的、反俄罗斯的和其他种种民族主义现在极其盛行。旧的兄弟般的信任的关系破裂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削弱了。显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政府(孟什维克)、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政府(木沙瓦特党人)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政府(达什纳克党人)存在三年之久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民族主义政府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向劳动者灌输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致民族主义的仇视气氛包围住了这些小国中的每个国家,使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得不到俄罗斯的粮食和阿塞拜疆的石油,使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得不到经过巴土姆运来的商品。至于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战争)和互相残杀(亚美尼亚和鞑靼的互相残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民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毒素的环境里,原有的国际主义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意识遭到了民族主义毒素的侵害,这是不足为怪的。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残余在工人中间还没有被铲除,这种情况(民族主义)就成了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活动方面联合起来的极大障碍。”
斯大林在此反映的问题绝非虚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各地经历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包括苏俄内战和外敌干涉,已经独立的各民族国家虽然逐步为苏维埃政权所控制,但相互之间的民族矛盾并没消除,在如何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问题上也各有想法。所以,斯大林在此所论的确反映了他对这些情况的忧虑,也将属于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看得更多。
虽然斯大林在“边疆”民族地区谈到的主要是地方民族主义,而在其他相关场合就也讲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了。如他在年2月10日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中就讲道:
“边疆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阻碍了党在这些地区的正常成长。一方面,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党员是在‘统治’民族存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压迫,往往缩小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者完全不重视民族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考虑某一民族的阶级结构、文化、生活习惯和过去历史的特点,因而把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庸俗化和歪曲了。这种情况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另一方面,当地土著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苦难时期,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压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抹杀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者把某一民族劳动者的利益和这一民族‘全民族的’利益简单地混淆起来,不善于把前者同后者区别开来,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也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的形式(在东方)。”提纲“坚决斥责了这两种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害的和危险的倾向,认为必须指出第一种倾向即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是特别危险和特别有害的”。
这里斯大林没有用规范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概念,但基本内容都有了,也将二者的顺序摆正了,即两种倾向中,“第一种倾向即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是特别危险和特别有害的”。当然,还有之前提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就和列宁的观点合拍了。这些观点,斯大林在其后的著述中做了重申,但一些地方有所变动,比如,上述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就正式写成“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将“地方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应,两种民族主义的提法也便正式形成了。此外,在斯大林看来,“民族主义”只符合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情况,而俄罗斯民族由于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所以不存在民族主义,而只有“沙文主义”。这和列宁的提法是不同的,列宁对相应情况更多表述的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是在其晚年才出现的。
年12月底苏联正式成立,同时新国家面临的任务和实行的政策也有了重大改变,特别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使得整个苏联的经济结构、社会心态都在发生变化,而作为一个新生的多民族联合政权,如何处理其中的民族关系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根本问题。因此斯大林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对影响民族关系的两种民族主义给予了格外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asaibaijianga.com/ajdc/8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