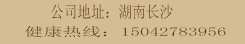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旅游 > 四十年情系突厥语词典,一生都在做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旅游 > 四十年情系突厥语词典,一生都在做

![]()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旅游 > 四十年情系突厥语词典,一生都在做
当前位置: 阿塞拜疆 > 阿塞拜疆旅游 > 四十年情系突厥语词典,一生都在做
⊙潘帅英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喀什)
[摘要]校仲彝是我国当代民族语言学家、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理事、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突厥语词典》汉文版的主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厥语词典》翻译与考订”的申报者、首席专家,一直致力于新疆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文学、翻译及研究工作,除了汉语和维吾尔语外,还自学并掌握了哈萨克、俄、英、德、土耳其、乌孜别克、塔塔尔等语言,对新疆境内语言及古突厥语、回鹘语、察合台语的研究也有一定造诣。校仲彝研究员接受笔者的采访并强调,《突厥语词典》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经典,编著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新疆喀什人,希望国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对这部经典的研究中来,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关键词]校仲彝;民族语言;《突厥语词典》;翻译与考订
年11月,恰逢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突厥语词典》翻译与考订研究”成功立项之际,由于博士论文涉及《突厥语词典》的多维翻译理论研究,笔者两次前往校仲彝先生家拜访,就《突厥语词典》的诸语种译本及《突厥语词典》汉译本的相关情况及“《突厥语词典》翻译与考订研究”中涉及的汉译本的重译等问题进行访谈,根据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并经校老本人改定。
潘帅英(下文简称“潘”):校研究员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专访,分享您与民族语言及维吾尔经典巨著《突厥语词典》的情缘。从您的生平简介来看,您祖籍湖南岳阳,出生于湖北宜昌,作为一名南方人,我很好奇您怎么选择了西北民族学院的维吾尔语专业?除了维吾尔语,您还学习了其他民族语言吗?
校仲彝(下文简称“校”):年我在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维吾尔语专业,当时我的理想院校是哈尔滨工学院,理想专业是工科或理科,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曾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当时想学自己的理想专业是很困难的,虽然我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单独考试且成绩较好,但仍没有被录取,高考分配时被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维吾尔语专业录取了。那时候,我对维吾尔族一点儿也不了解,只是在学校组织的晚会上听到过一位女同学唱过新疆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由于专业不是自己选的,不是很喜欢,不甘心学这个专业,甚至想重新参加高考,来年再报考理工专业,但有老师恳切地宽慰我:事在人为,只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肯定能在这个冷门专业上干出名堂。家人也劝我说,理想的大学来年也未必能去,不如就学这个专业,说不定也会有另一番光景的。于是,18岁的我扛起行李去了兰州,静下心来学习维吾尔语。
当时,我们教室的两边都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和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同学的教室,有着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经过近1年的学习,我掌握了一般的维吾尔语对话,也结交了许多少数民族同学。学习维吾尔语专业的同时,我觉得哈萨克语听起来也非常优美,于是还自学了哈萨克语。经过刻苦学习,我的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
潘:作为一名民族语言汉译工作者,除了要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还需要深厚的汉语语言功底。拜读您汉译的论文、译著,以及新疆作家郭涵在《点赞新疆人》中用约4万字的篇幅为您撰写的报告文学,得知您的汉语语言功底源于幼时的启蒙、青少年时期大量且广泛的经典名著阅读,能请您谈一下学习汉语和阅读经典的情况吗?
校:我十分感谢小学(1至4年级)时的启蒙恩师,除传授课本知识外,他一直严格要求学生每天坚持写日记,坚持每天给学生们讲两三个故事(从远古时代到抗日战争时期,如三皇五帝、圣贤、英烈、诗词名家、文化名流、近代抗倭英雄、抗日战争中的名将等),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大的收获,老师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头天讲过的故事,第二天每个学生复述故事梗概;二是头天布置的诗词和名言名句,第二天必须会背诵。否则,第二天就不给讲新故事。老师的用意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学生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同时又锻炼了学生们的口头表达能力。此外,家人对我的学习也非常支持,给我购买了大量古代和近现代图书及词典,我不仅浏览一般的章回小说,还阅读过四大古典名著。
中学6年,我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学习数理化和俄语上。课余时间或者周末,我最喜欢待在图书馆,因此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文学名著。我那时候就读过《荷马史诗》《伊索寓言》《鲁滨孙漂流记》《巴黎圣母院》《安徒生童话选》《基督山伯爵》《羊脂球》《牛虻》《约翰·克里斯朵夫》,特别喜爱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喜欢《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更喜欢背诵雪莱、拜伦、泰戈尔、海涅等人的诗作,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母亲》《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普希金等人的诗作也很着迷。由于学习俄语,我也阅读背诵了不少俄语原著的片断和诗歌。
我觉得经典著作是导师、良师,带我前行;是挚友、益友,陪我前行;是楷模,是榜样,催我前行,激励我奋进。广泛阅读中外经典名著为我的汉语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后来从事民族语言的汉译工作夯实了语言表达的功底。
潘: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维吾尔语专业,毕业后从事了什么工作,后来如何又来到了新疆?
校:现代维吾尔语划分为3个方言区:中心区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中心区方言是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基础方言,新疆伊犁地区的方言属于中心区方言。年2月28日,由老师带队,我和其他同学一行40多人乘上了从兰州开往新疆的火车。3月9日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所在地伊宁市。3月10日,40多名同学绝大多数分别去了离伊宁市数十公里远的维吾尔族群众比较集中的农村,住在农户家中,我被安排在伊宁市,给市委宣传部张部长当秘书兼翻译。新疆伊犁地区的环境特点是民族成分多,语言种类多,居住着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锡伯、回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我每天除了陪同张部长参加会议或外出活动之外,还可以和周围的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群众自由交谈。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学习语言的老师。我随身带笔记本进行记录,半年实习结束后,记录了满满6大本笔记,这可是在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伊犁是哈萨克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我在大学自学的哈萨克语刚好可以在这里实习。
很快,我的哈萨克语会话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不仅如此,我的俄语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同时,我也接触了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和塔塔尔语,觉得这里是学习多种民族语言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来新疆工作,要掌握更多的语言,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
4年的大学学习生活结束后,面临毕业分配问题。老师们都希望我能留校任教,我却对去新疆十分向往。但我不能自作主张,后来学校组织部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学校要从甘肃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招收60多名哈萨克族学生,学校的几位哈萨克族领导和老师推荐我留校任教,教哈萨克语。为了提高哈萨克语教学水平,我特别订阅了哈萨克斯坦的文学杂志《星》(月刊)和新疆的哈萨克文文学月刊《曙光》,还阅读了不少国内外出版的哈萨克文著作和报纸。经过两年的努力,这些连一句汉话也不会说,一个汉字也不认识的哈萨克族学生渐渐可以用汉语对话,也能听懂汉语教学了。我第一次工作取得了好的成绩,颇有成就感。
也许是对新疆的向往使我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年暑假,我在与新疆乌鲁木齐的同学和朋友们交谈之时,大家向我提出来可否来新疆工作之事。年11月初,我如愿调到了新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室工作。我激动不已,提笔写下了“西出阳关誓不悔,扎根新疆不东归”的诗句。
潘: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室主要从事哪些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主要从事了哪些工作?后来是如何与《突厥语词典》结缘的?最初从事《突厥语词典》汉译工作的情况如何?
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有30多位工作人员,9个民族成分,学术氛围很浓。工作任务就是研究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制定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方案。我们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要通过对语音、词法、语法的深入研究,结合新文字字母的确定,进行更细致的具体研究,结合实用要求,制定文字改革方案。此外,我还参与创办专业刊物《新疆文字改革》(月刊),刊物的出版发行为全面推进文字改革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受杂志社编辑部的委托,我用维吾尔新文字编写了《维吾尔语法十二讲》,准备在《新疆文字改革》上连载,后因“文化大革命”,杂志停刊。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我坚信当时的社会乱象总会过去的,更应该抓紧时间学习,自己不能混日子。年,“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很响,年10月,我被派往上海,与上海打字机厂联系,商讨新疆生产能打出维、哈新文字的打字机事宜。经过2个月的努力和文字方面的技术指导,新打字机陆续生产出来并运抵新疆。年底,自治区革委会文卫组(相当于宣传部)组织召开了“自治区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推行工作大会”,为规范维、哈新文字的新词术语成立了工作组,由我负责维、哈新词术语研究审订工作。年年初,我提议应当用新文字编写《汉维词典》《汉哈词典》以及《维汉词典》《哈汉词典》。年5月初,我和另外三位工作人员被抽调到自治区党校,开始《汉维词典》编写工作。年6月,书稿交付新疆人民出版社。年12月,词典正式出版发行。
年春,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风也吹拂了新疆大地,维吾尔族经典巨著《突厥语词典》的研究与翻译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当时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审订《哈汉词典》,阿不都萨拉木·阿巴斯主任让我加入《突厥语词典》汉文翻译组。最初《突厥语词典》汉文翻译组共有3人,除我之外,还有何锐(组长)和陈宗振。最初的时候还有李经纬先生,后来他因故退出了。年1月,陈宗振返回中国社科院工作,何锐退休之后,我独自一人投身艰巨的《突厥语词典》汉文翻译工作。年年底,我完成了第一卷的修订和统稿工作;年至年,我先后完成了全书70%至80%的翻译工作,并完成全书译稿的修订统稿工作。
潘:《突厥语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语词注释突厥语词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突厥语词典》汉译本是您主译的,如今您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厥语词典》翻译与考订”成功立项,您是不是想通过考订,重新对《突厥语词典》进行汉译?为什么想对这部经典进行重译?
校:年开始翻译时,我是以维吾尔文译本为蓝本,并参考了土耳其文和乌兹别克文版本,而维文本主要是根据乌兹别克文本转译的,因此,汉文本是转译的再转译。参与翻译的课题组成员不懂阿拉伯语,而《突厥语词典》是用中世纪阿拉伯语注释古突厥语词的双语词典。由于不懂阿拉伯文,首先无法考订正确的词条数目,当时依据维文本,汉文本共有个词条,年维文本修订后增加至余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方面知识欠缺,加上自学的阿拉伯语水平也不够,我不敢对许多词条妄加注释,因此汉文本全书几乎没有注释,而在国际学界一致认为较佳译本的英文本有许多注释。
除此之外,汉文本(维文本也是)音标采用了废弃不用的维文新文字字符,其中一些字符不便识别,也不便书写、排版,且汉文本的阿拉伯文存在不少错误,如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姓名的汉文译名也不一致,许多质朴、灵动的突厥民歌、情歌被人一时兴起改成了汉家仕女画般的柔媚娇态,哪里还有中世纪突厥人狂野、刚强、率真的美?重译《突厥语词典》时,我将重新撰写约4万字的序言,并根据突厥语原文把数百首民歌和谚语译得更准确、更优美。
年,我把汉文译稿全部送出去后却丝毫不能感到释然。我记录了全书数百处问题,但无法解决它们,因为我不懂阿拉伯语,只是自学了一点儿阿拉伯语法。一个人竟敢去翻译连自己都不懂的文字,还竟然译了其中70%至80%!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歉意,想设法把自己没有做好的工作重新做好。
潘:《突厥语词典》抄本问世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转载请注明:http://www.asaibaijianga.com/ajly/5536.html